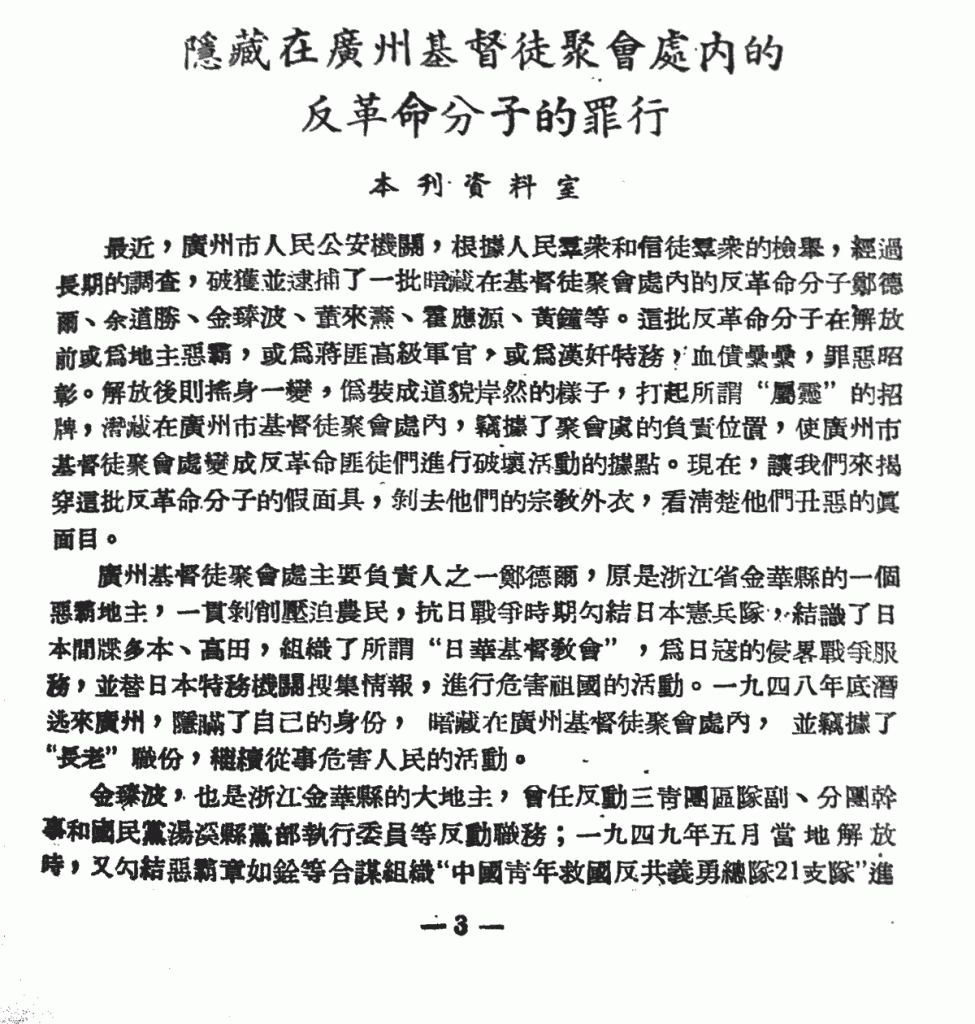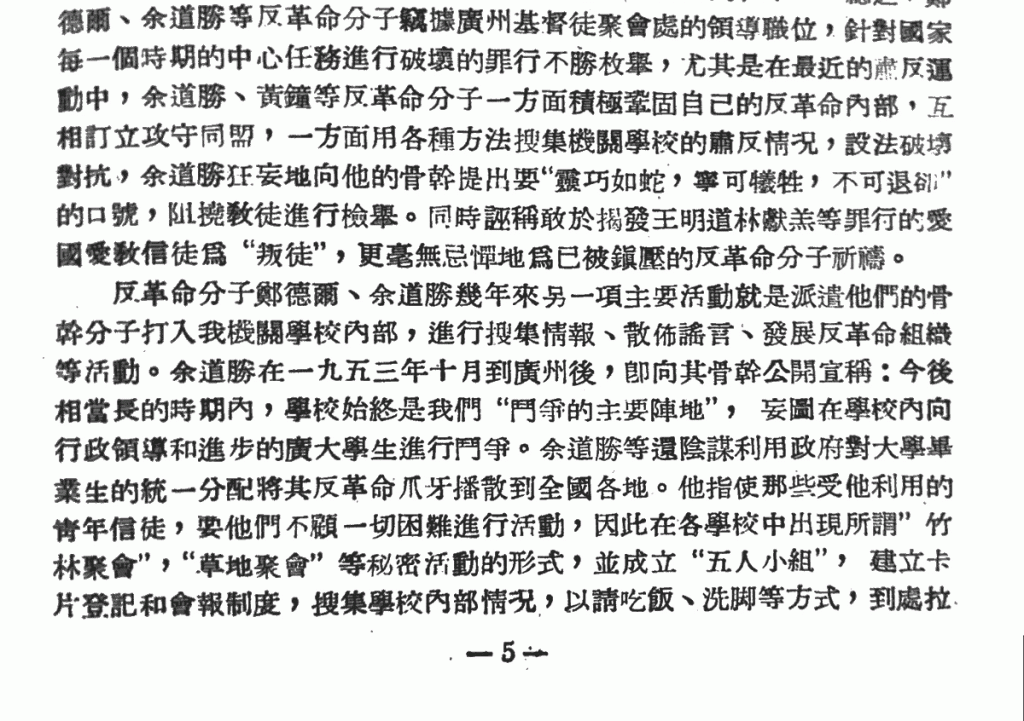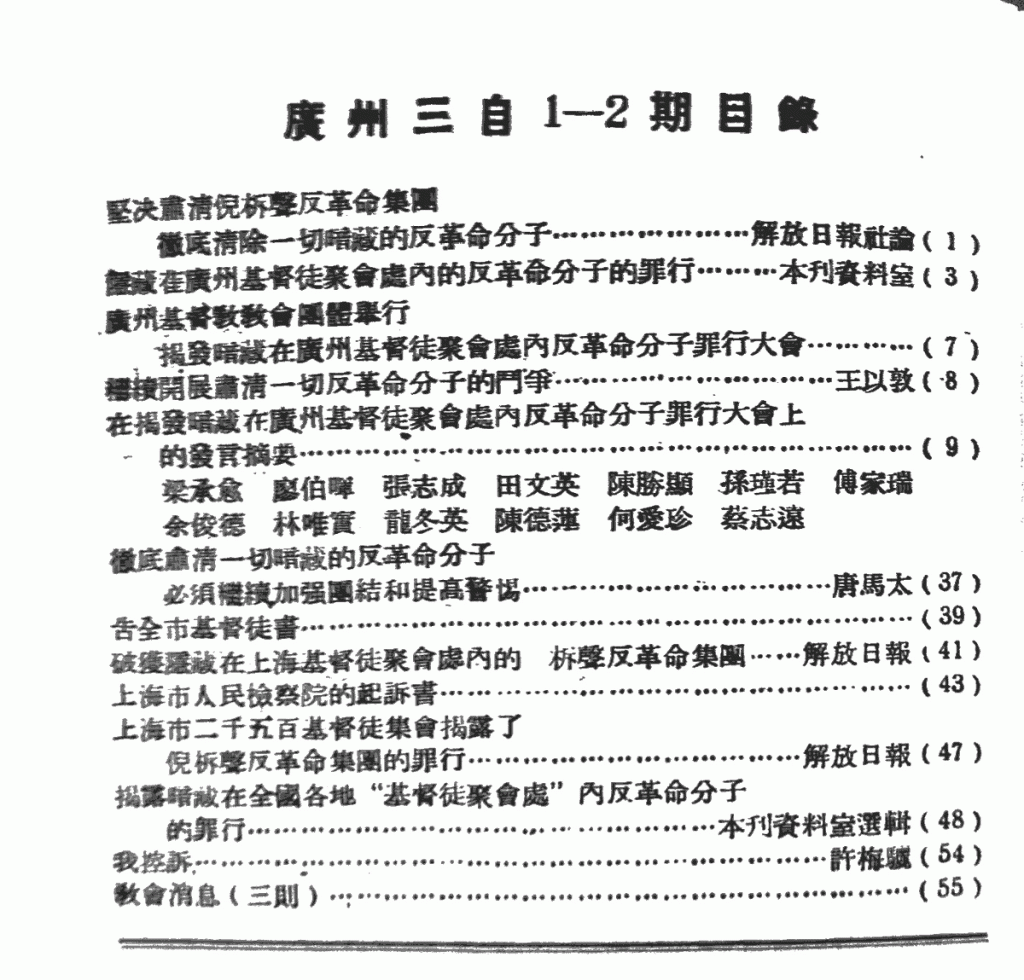余道胜妻子余李晋玲的见证
Comments Off on 余道胜妻子余李晋玲的见证我是一个第三代基督徒,祖父祖母在山东烟台听见福音而信主。祖父祖母很爱主,每天睡觉前,两人先到西屋跪下祷告后,才入睡房就寝。父亲生病 ,祖母来看他,跪在地上为他祷告。我的父母也很爱主,我们家有家聚会。我小时候曾祷告,如果以后像父亲那样有钱,也要盖礼拜堂。一九三几年,倪弟兄来烟台讲道,我的父亲、二姊、三姊都去听,觉得很好。后来,堂姊去了上海,和倪弟兄一起聚会,参加过友华村训练。
,祖母来看他,跪在地上为他祷告。我的父母也很爱主,我们家有家聚会。我小时候曾祷告,如果以后像父亲那样有钱,也要盖礼拜堂。一九三几年,倪弟兄来烟台讲道,我的父亲、二姊、三姊都去听,觉得很好。后来,堂姊去了上海,和倪弟兄一起聚会,参加过友华村训练。
一九四二年,我在上海读大学,暑假回到烟台,家母为我的得救禁食祷告。当时连着一周每天都有聚会,周六那天读圣经讲受浸,那些话一直跟着我,睡觉、吃饭,在我里面作工。我到一个没有人的房间跪下来,一跪下就像浪子回了家,眼泪不停的流。主在里面就催促我去受浸谈话,受浸谈话时李弟兄问我,“李小姐,你爱主吗?祷告吧!”那个祷告真是甜美。第二天主日,我就受了浸。因着主在里面的带领,受浸之后,我的梳头发、穿衣,都有了改变。过了几个月,到四三年,烟台大复兴。大家都很受感动,我也受感动把自己交出来。
四六年我又到了上海,当时抗战刚胜利,许多弟兄姐妹还在外地没有回来,祷告聚会没有几个人。不久后倪弟兄回到上海,上海的事奉也上了轨道。汪佩真姊妹有段时间对我很有负担,叫我住在她那里,现在回想起来,那是对我在生活上、在各方面的一个训练。汪佩真当时对我很严厉,我受不了,有一天早上,汪姊妹说,“我们早上吃过早饭后,大家到厅里面有点祷告”。那天祷告她哭了,她对我说,“我盼望主在你们青年人身上有路”。她那样一哭,我里面就转了。
四八年,倪弟兄在一次全国同工的聚会中,要我和周靖梅姊妹放下职业事奉主。当时上海教会要在四个地方同时传福音。我参加了第二期的鼓岭训练,倪弟兄的信息很有光,我觉得很蒙恩。
五○年上海福音书房的服事者李渊如姊妹写信到福州,叫我回去帮忙。我回到上海,帮忙把鼓岭训练的信息出书。《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的神》、《什么是新约》也出版了。五二年我在福音书房配搭排版诗歌,有时遇到问题,李渊如姊妹就叫我去问倪弟兄。倪弟兄那时心脏不好,躺在家里,倪师母在那里照顾他。第二次我去的时候,才到门口,倪师母就出来,要我快离开那里,她说公安局的人在里头跟倪弟兄谈话。那天下午,倪弟兄就被公安局的人带去东北了。
五三年,我与余道胜弟兄结婚。余弟兄是上海交通大学毕业的,四七年毕业后在外省工作了一年,后来辞掉回到上海参加交出来的聚会,训练完被倪弟兄打发到云南、昆明一带服事。五○年,余弟兄的父亲希望他结婚,他回到上海请当时年长的同工俞成华、张愚之、朱臣、李渊如等人为他的婚姻祷告,祷告了两三周之后,他们都觉得我们两个人合适,李渊如姊妹就来跟我题这件事,我们就在五三年十月结婚。结婚后我们到广州去看余弟兄的父母。余弟兄到了广州后,学生人数多了起来,引起政府注意。有一天宗教事务处把余弟兄找去,叫他停止讲道,不然后果自负。余弟兄回家后祷告了一个礼拜后,回宗教事务处说,“我已经奉献给主了,无论得时不得时,务要传道”。
五五年底、五六年初,广州开始肃反运动,打击“广州倪柝声反革命集团的首恶份子”,余道胜弟兄和郑德尔、霍应源等人一同被抓。先关了一年,然后下放农场两年,之后又派去化工厂。名义上是化工厂,其实就是劳改场。像余道胜这样不肯放弃信仰的劳动比较苦,要替锅炉铲煤,还要去洗隔壁小学的厕所,后来又要他用硫酸、盐酸洗产品,手常常流血、流脓。不仅如此,还要他们批判圣经。有一天余弟兄从工厂回来,吃不下饭,我问他为什么,他说下午他们要他发言批判圣经,我们就一起祷告。多奇妙,到了下午,他们把题目改了,改为批判国家的副主席。
由于环境所逼,余弟兄只有离开大陆。他走后,因着传福音,我被关进监狱,原本要判十年。一年后,华国峰任主席,落实党的宗教政策,我被释放。之后我与两个女儿被送到农村。那时大女儿才十五岁,必须跟当地的农民一起劳动。
一年之后,主开路,我们回到广州。余弟兄后来辗转从香港到了美国。感谢神,因祂奇妙的恩典,我们母女也于八○年代来到美国,一家团圆。
余李晋玲
以下是当年陆弟兄被捕时,报章媒体的报导: